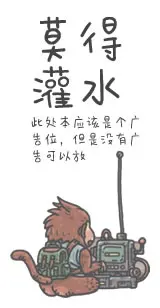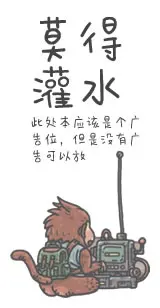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
打捞
在开场的鼓点响起时,我站在酒吧门廊上向里面望去。
各色的塑料方椅包围着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每一张椅子上都坐着一名年轻人,这是最热闹的一个晚上。台上的麻花辫鼓手环视观众席,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却有一滴汗从他带有伤疤的额头滑落。身后充当幕布的橘黄色防水布被突然掀开,一名矮小的青年从后台钻出来,起须的裤脚摩擦着地板,随着他踏过发出令人窘迫的声响。小个子青年凑到鼓手身边,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
鼓手的笑容逐渐消失,被烈日曝晒过的脸颊变得更红,那是他发怒的前兆。
躲藏在阴影中的我,在被他们发现之前,安静地走出了酒吧。
老化的金属门板在我身后关上,鼓声再次响起,我长舒了一口气。
酒吧门口的告示栏被层层旧传单糊满,最上面的是一张演出海报,由于张贴得十分急迫,纸张微微发皱。乐队的名称十分蹩脚,像是从英语里随意拣拾出两个含义不羁的单词拼凑在一起。照片是用老式胶卷相机在一间冷冻仓库里拍摄的,盛装着鱼和贝的白色泡沫箱在背景里堆得很高,像一面千疮百孔的墙。几名乐手刻意地别开脑袋回避镜头,姿势僵硬。被他们围在中间的女孩身穿破洞的黑色裙装,刷了珠光眼影的眼皮在灯下像两片鱼鳞。她岔开双腿用力绷直,麻木地看向镜头,脸色因低温而显得苍白,表情则被浓妆淹没。
我从口袋里拿出黑色的唇膏,用力按在女孩的脸上。将海报涂花后,我把唇膏扔在地上,朝海边跑去。
深夜的岬岸空无一人,椰树的影子被月光拉长,有开裂的果实碎在阴影里,流淌出的汁水迅速被沙地吸收。几艘渔船安静地停泊在海湾中,我在一根船墩上坐下,甩掉脚上的尖头高跟鞋,脱掉裹住小腿的黑色网袜,摘掉脖子上的水钻项链,一样样扔向大海。鞋子立即沉入海底,项链漂浮片刻也消失在了水中,唯独黑色网袜轻飘飘地落在沙滩上,被碎石勾住,没能被海浪卷走,黑暗中像一团纠缠的水藻。
留在岸上的垃圾比海里的垃圾看起来更加寒酸。
我决心不再看它们,而是望向海面。暴风季刚刚离开,波涛若无其事舔舐沙滩,海面平和的样子不像上个礼拜才吞噬了两名水手。正是这种无耻的姿态让青年们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离开,来摆脱被水母缠足沉入海底,或是被坠落果实砸碎头颅的命运。至于那些无法离开的人则会采用更加盲目的手段来进行对抗,比如留长头发编成辫子,比如学习某种乐器,比如组建一支拙劣的乐队,用没人听得懂的音乐来宣泄自己的无能。
而我则正是这拙劣乐队的一员。今晚我本应站在那个狭窄的舞台上,对着失真的麦克演唱那首我们练习了半年之久的歌曲,但此时,我却独自坐在岸边,将酸痛的脚趾埋进沙子,对着空无一人的海面放声歌唱。
船晃动了一下,我立即止住声音,屏住了呼吸。
一个陌生男人打开船舱,摇晃着来到了甲板上,在木桶上坐下。
他闭着眼睛,看起来十分困倦。我不敢开口问他是否是被我的歌声吵醒。
男人低头衔上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他的手遍布皱纹,看起来比他的面孔更加苍老。被渔网割破过无数次的手指,经过海水的浸泡变得粗糙而强壮。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后,他终于睁开双眼看向我。
“你为什么在这里?”他问道,仿佛对我非常熟悉。
“你认识我?”
“这里的所有人都认识你。”他的语气没有任何嘲讽或恭维,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没有回应。
他的视线落在海滩上,看到了我扔掉的网袜,似乎明白了什么。
“没有歌手,演出是没办法进行的。”他说。
“没有我在,他们仍然可以照样演奏。”我告诉他,“他们不关心我唱什么,只是需要我站在那里。我唱得又不好听,只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人才会让我上台。”
没那回事。我期待男人能这样反驳我,但他只是垂下眼睛,一言不发地吸了一口烟。
海边的空气咸涩而潮湿,我的睫毛膏开始融化,我用手去擦,手背被晕开的眼线染黑,眼皮则变得更加黏着。我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难听,像我唱过的每一首歌。男人则坐在甲板上,不吵不闹,只是沉默地抽烟,像一名忠实的听众。
不远处逐渐出现了喧闹声,我听见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我慌忙止住声音,下意识看向男人。
他挥手将没吸完的烟扔向海滩,烟头落在被我丢弃的黑色网袜上,燃烧起来。我们安静地望着火焰在砂砾上跳动,直到熄灭。他站起身,船只摇晃着掀起波浪,海水涌上沙滩,卷走了残留的灰烬。他来到甲板边,用打捞浮木的姿态,向我伸出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