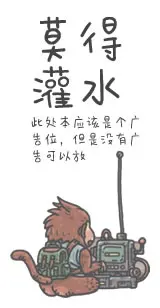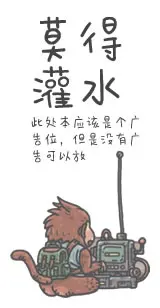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
喜丧
一天前,老板就贴出了告示,今天码头歇业。 他要在这里为自己的父亲举办葬礼,据说那个善良的老头创办了这个码头。 现在他死了,而我对这个老头,除了善良之外并没有其他印象。原因是我刚到这个码头的时候他给我准备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还有一双手套。 手套已经烂了很久了,而我也决定离开这里,因为在一个除了海风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停靠的码头做搬运工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成家立业的工作,至少我那两个同样善良的父母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决定参加完这个老头的葬礼,就离开这里。 所谓的葬礼,参与者中的大多数其实比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要更加开心,毕竟他们未必有生日宴会,但葬礼却时常有。 我和师傅,还有码头其他自愿来帮忙的工作人员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我们负责葬礼现场的大部分布置。一个仓库被用作临时的礼堂,老头的尸体放在冰柜里,摆在礼堂的正中央,他此时的脸部已经呈现出一种奇妙又不可言喻的蜡黄,或许是人多的缘故,和平时搬的货物箱相比,搬起一个小老头的尸体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费力。 冰柜与大门之间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写着"奠"字的圆形的屏障,两边放着两个花圈,前面的小桌子上放着老头的遗照,我废了一番功夫才把照片上的人和躺在冰柜里的那个人联系起来。遗照前面是三根巨大的蜡烛和一些值钱,还有馒头,苹果这些贡品。 最后在门外搭上棚子和桌椅,葬礼的主要会场就完成了。 现场布置完后,首先来到的是丧乐队,他们没有做祭拜,而是直接坐在外面吹奏起来,唢呐声,鼓声,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乐器的声音混合成浑厚有力的交响乐刺破天际。他们就这样每隔半个小时吹奏一次,循环又循环。 老头有四个女儿,她们坐在尸体的旁边,有人来祭拜便哭上两声,没有人来时则是在闲聊。内容是谁家的女儿嫁了个好人家,而谁家的儿子还宅在家里连女朋友都没有这样的家长里短。 老板作为老头唯一的儿子,接待来宾和统筹整个葬礼的任务很自然的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一边催促来迟的做饭阿姨,一边给刚到的丧乐队发香烟,一边笑着回应来客"听说你家儿子考上博士了,真了不起啊"诸如此类的恭维。 随着饭点的邻近,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甚至渐渐盖过了丧乐队的交响乐。 并不需要老板招呼,当饭菜摆满餐桌时,每张桌子上的人就自觉动起了筷子,于是又是一番新的吵闹。 隔壁桌少了一份红烧肉,还没有闲下来的老板赶紧催促这后厨阿姨补上,而桌上的一个中年人则大声回应"不用招呼啦,赶紧坐下来吃饭吧。"
靠近海边的一桌上的小孩嫌弃海风夹杂的鱼腥味太臭吵闹着吃不下饭,我赶紧去把那边的棚子关了起来挡住海风。不过他还是吃不下饭,也依旧吵闹着。理由是他们桌的果粒橙喝完了。 坐满男人的那桌开始劝酒了,有人劝,有人推脱,最后还是"难得见一次,不能不给面子"这样的劝酒理由压倒了所有的推脱借口。 晚饭顺利的结束,老板像是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又开始安排晚上守夜人的活动,妹妹和妹夫们在一起想想办法凑一桌麻将,侄子侄女侄女婿们在一起想想办法凑一桌炸金花,孩子们的安排则最容易,只需要给他们手机就可以了。 我去把靠海那边的棚子打开,海风夹杂着海水的清香和死鱼的恶臭报复性地扑面而来,恰在此时,丧乐队的交响乐又响了起来,不知名的音乐抵抗着海风,最后又随着海风一起飘到海面,飘上了天空。 今天是葬礼的第一天,葬礼还有两天,但我决定明天就离开。 我来到自己的宿舍准备收拾行李,却发现桌子上有一块小蛋糕,旁边放着师傅和工友们给我凑的500块钱。 原来如此,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