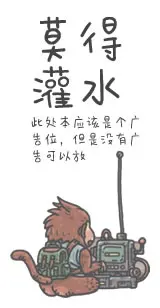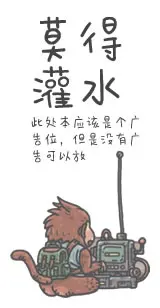这一篇的稿子在几年前就收到了,但是作者对剧情和文笔方面一直不满意,就没有发表。直到几年后的今天,还是决定从记忆的角落把它翻出来,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算是一个归宿吧。
海平线
作者——竹勿言 如果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了,你会做什么呢? 曾经,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本子上有类似的处境,主角无所事事地荡去学校,遇上女孩儿。天空染成一片红色,巨大的陨石下,他们做爱了。
当然,本子里总是要做爱的。可我不免想到自己——年已十八,尚是处男。最后一次天气预报说,(说来可笑,向来不准的预报唯有这次准得很)陨石将在今天傍晚五点落下。 我下了客厅。母亲双腿交叠,单手持书。父亲站在阳台处,双手负在身后背对着我。 “我要出去一趟。” 我说。 妈妈抬起头。 “去哪?” “就是出去走走。” “早点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 “你不担心我吗?” “担心啊。但担心能阻止你出去么?” 我摇头。 “而且,你才十八岁,但你就要死了。会有什么想去做的事吧?” 话语脱口而出。 “如果我想去杀人呢?” “那就去杀。” 我吃惊地说不出话来。 母亲又说:“早点回来。” “好。”顿了顿,“我不是去杀人。” “我知道。” 我当然不是要杀人,我只是想上街,随便找一个女孩儿做爱。或许到了现在,做爱已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和吸毒、抽烟、打游戏或任何即时享乐的行为没有任何区别。父母学生时代便拍拖了,然后有了我。他们做爱想必是为了有一个孩子吧。 母亲是一名大学老师,父亲是一名司机。有了孩子,母亲一生便只能被绑在家庭中。年轻时,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然后在某个欧洲国家开一家咖啡店。如今闲暇时,母亲便在家里看书。在我小时候想必更忙,换尿布,哄我睡觉。五岁前,我体弱多病。父亲开着他那辆老旧的标志四处载客,无暇管我。母亲便从学校请假,带我去医院。我觉得是自己夺去了母亲在欧洲开咖啡店的未来。有一次,我问她为何要那么早结婚。她说,那时候看父亲打篮球很帅,喜欢上了他。长大后就结婚了,没有想那么多。我问她后不后悔。她回答,到了现在,已经不会再想这些东西了。 现在,我正走在街道上。铁网被往来的小孩儿图近路剪开了口子。树根狰狞地吸住了泥土,沥青丑陋地向上凸起,裂开;对面的人行道,有两个人在打架。马路空荡荡。熄了灯的车辆停在路边,灰尘薄薄一层。我独自徘徊,没有行人,更遑论想要找到一位游荡者,她也恰好是为了想要和某人做爱而踏上路程了。 我掏出打火机,点上一支烟。火苗左飘。这说明风从西边吹来,往东方而去。 职中退学的那天,我坐在江边的栏杆上点上十六年以来的第一根。那时,脑海里浮起的是几年前,爷爷拒绝了化疗,奶奶将他接回家,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他时常咳嗽,随身带一痰盂,从身体深处呕出带血的痰。奶奶劝他戒烟,爷爷便在奶奶出去时偷偷点上一根。吸几口,咳几声。吸几口,咳几声。 一个男人站在电线杆前撒尿。男人有些尴尬,但尿还没结束,它在空中划过一道半圆,撞到杆子,溅向周遭。
他向我打了个招呼。 “嘿。” 我点了点头。 他不在意,自顾自往下说:“真不可思议,是么?一个月前我还在手机发布会上演讲,一个月后世界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得死。” 这时我注意到了,他似乎是小米的老板,雷军。但我不确定。 他结束了,晃了晃那玩意儿,提上裤子。 “我一直很想这么做。”他解释,“往电线杆上撒尿。可惜现在街上没人了,加上你,只有两个人路过。这也不错,你懂得,没人看见就了无生趣。你呢?你想做什么?” “做爱。” “做爱?噢,我懂了。是不少人这么做。而且在这种环境下。那你做了么?” “我还在找。但我一路上就看到你,还有两个人在打架。” 他有点惊讶。 “找?意思是你还没约好么?” “是没有。但既然有十八岁的处男想破处而瞎逛在街上,应该也有十八岁的处女想破处而瞎逛在街上吧,我猜。” “恩……”雷军沉吟,“本来我想介绍你一个场所,那儿全是做爱的人。可你想要的不是那样的对吧?” “可以这么说。” “你记得我刚刚说的话么?除了你,大概是五分钟前,我还看见一个人。那是一个女生,我没向她搭话。毕竟是女生嘛。她去了那边。” 雷军指了指前方。 我向他道谢。 “不用!毕竟那是你的愿望嘛,和我想要在电线杆上撒尿一样。祝你好运。” 上坡不是很陡,路的两边是居民的房屋。一个女人往长线上晾晒衣物。男人坐在门槛上发呆。路边,遗失的传单没了骨头似地翻滚。远方,烟囱缕缕冒出黑烟。 我想,即便是下一刻大家都要死了,人类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多改变。要吃饭,要晾衣服,要撒尿。刚才,我看见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比起他来,我或许是幸运了很多。我已活了十八年,就算再活几十年也不一定会比这十八年更加充实。可是,对于那个婴儿来说则有些不公平。才出生没几天,见识不到世间或美好或丑陋的一切便要就此死去。如果可以,我想问问那位母亲,如果早知道这样,你还会把她生出来吗?或许她也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应当问问那个精子,说:嘿,恭喜你在几亿的同胞厮杀中胜出,成功和卵子结合在一起。可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两年后,也就是你刚降世一年多一点,一颗陨石就会砸下来,地表上的所有人类都会死光光,包括你。你怎么想?你还想熬过十月怀胎,然后出生吗? 我拐过两道湾,走过一条小巷,绕过小溪,踏过数不清的人行横道。现在,周围已荒芜起来。大马路宽阔而空旷。路的两旁栽满树木。几间废弃的厂房建在树林里,墙砖剥落,开在顶棚的窗户爬满绿色的青苔。很早就偏离方向了。可我并没有故意寻她。如果她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儿,那她自然会出现。而如果她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儿,就算找到也没用。 风咸咸地,且凉。海岸就在前边不远了。路面逐渐潮湿,沙子粘在铺满路面的石子的缝隙里。烂了的渔网趴着。死鱼浮在还有浅浅一点水的水箱里。这儿曾是一个海鲜批发市场,整个镇上,乃至整个省的人开着汽车,货车来到这里。它们是几个月前来这里捕鱼的人们留下的。 长长的石墩无限延伸。沙滩在那边,马路在这边。海天一色,细浪扑来又卷去。女孩儿站在浅滩处,海水淹没了脚踝。
我跨过石墩,走到她身边。 女孩儿眺望着远方。 我仔细端详她。 脸颊微胖,是那种看了令人放松下来的胖。眼睛是蓝色的。鼻子普普通通。嘴唇小巧红润。我不知道旁人怎么评价,但我认为她很美。 “你在看什么?” 我回答:“看你。”又问,“你在看什么?” “自己看。”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夕阳半沉于海平线尽头,烧云点着了整片天穹,浪尖烁烁闪动。 “怎么样?” “很美。” 她扭过头来,我也恰好移开视线。她的蓝色瞳孔里是我的瞳孔。 我们异口同声。 “我是处女。” “我是处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