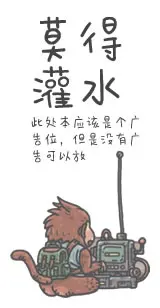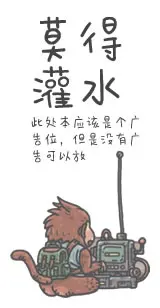豆瓣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838908153/?_i=5048206YR_1TYa ,5048372YR_1TYa
声明:翻译仅供推理小说爱好者交流使用,严禁用于非法商业用途。如需转载,请保留作者、译者,谢谢。
松溪镇的寡妇( 该篇目选自《傑佛瑞迪佛的黑色禮物》, 篇目名称采用台版翻译 )
杰夫里·迪弗/著 猫的薛定谔/译
“有时候帮助就是会从天而降。”
这是她母亲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并不是指天使、灵魂或任何新纪元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凭空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好吧,妈妈,希望如此,因为我现在就需要帮助,且能充分利用它。桑德拉•梅•杜蒙特靠着一张黑色皮革办公椅,手中的文件落在她已故丈夫办公室里的那张旧桌子上。她望向窗外,不知道现在看到的是不是那个施与她援助的帮手。
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走在通往工厂的水泥路上,一个面带微笑,目光锐利的男人。
她转过身,从她十年前在他们结婚纪念五周年日那天,给丈夫买的古董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而今她对那快乐的日子只有简短的记忆; 她现在一心关注的是她的形象:一个大块头的女人,虽然不胖,还有那聪敏的绿眼睛。她穿着一件印有蓝色矢车菊的灰白色连衣裙,无袖——这是在五月中旬的乔治亚州(佐治亚州)——露出了结实的上臂。她的深金色的长发梳在脑后,用一个结结实实的龟甲发夹固定着。只是化了点妆,没有喷香水。她三十八岁,但有趣的是她意识到,她的体重使她看起来更加年轻。
按理说,她应该感到平静与自信,但她不并没有,她又看了看面前的报纸。
不,她根本没有那种感觉。
她需要帮助。
从天而降。
或者来自任何地方。
对讲机的嗡嗡声吓了她一跳,尽管她正等着这声音。老式的装置,棕色、塑料材质,上面有十几个按钮。她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
她按了个按钮。“什么事?”
“杜蒙特太太,罗尔斯顿先生来了。”
“好的,让他进来,洛蕾塔。”
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说:“你好。”
“嘿,”桑德拉·梅自然而然地站起来回应道,她回忆起在南方农村,女人很少站起来和男人打招呼。同时也在想:我的生活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注意到,就像她上周末见到他时一样,比尔·罗尔斯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他棱角分明,黑发蓬乱,虽然很瘦,但身材似乎并不特别好。
还有那口音!上个星期天,当他们站在松溪镇乡村俱乐部的甲板上时,他笑着说:“最近怎么样?我是比尔·罗尔斯顿,来自纽约。”
好像他的鼻音没有挑明似的。
还有“最近怎么样?”,好吧,这可不是你从当地人那里能听到的问候方式(桑德拉·梅称他们为“松溪人”——尽管只是对她自己而言)。
“进来吧,”她对他说。她走到沙发前,掌心朝上,示意他坐在她对面。桑德拉·梅一边走,一边盯着镜子里的他,她注意到他并未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那很好,她想,他通过了第一个测试。他坐下来仔细看了看办公室和墙上的照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吉姆打猎和钓鱼。
她又想起了万圣节前夕,电话那头州警的声音,回荡着一种空洞的悲伤。
“杜蒙特夫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是关于你丈夫的……”
不,现在别想这些。集中注意力,你麻烦大了,姑娘,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帮你的人。
桑德拉·梅的第一时间的冲动是想给罗尔斯顿倒点咖啡或茶。但后来她停下了。她现在是公司的总裁,她有员工做这类事情。古老的传统难以磨灭——这句话出自桑德拉·梅的母亲,她就是这句格言的化身。
“你想喝点什么吗?甜茶?”
他笑着说:“你们在这里肯定更多是喝冰茶。”
“这就是南方能给你的。”
“当然,我还是喜欢来一点。”
她呼叫吉姆的长期秘书兼办公室经理洛蕾塔。
那个漂亮的女人——每天早上一定要花两个小时化妆——把门开了一个缝儿,探出头,“什么事,杜蒙特夫人?”
“请给我们来点冰茶,好吗?”
“乐意效劳,”那个女人离开了,留下一阵花香。罗尔斯顿对着她身后点点头。在松溪镇,每个人都很有礼貌,纽约人要花点时间才能适应。
“我告诉你,罗尔斯顿先生……”
“请叫我比尔。”
“比尔,这是这儿的第二天性。有礼貌。我妈妈说一个人应该像每天早上应穿戴整齐一样去对待礼仪。”
他对她的说教报以微笑。
说到衣服……桑德拉·梅不知道该怎样去看待他的衣服。比尔·罗尔斯顿穿得……很北方,只能这么形容了。黑色西装和深色衬衫,没有领带。正好与吉姆相反——他习惯穿着棕色长裤、浅蓝色衬衫和棕褐色运动外套,好像这套衣服是强制性的制服。
“那是你丈夫?”他看着墙上的照片问道。
“那是吉姆,是的,”她轻声说。
“真帅,我能问问发生了什么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罗尔斯顿立即明白了。
“对不起,”他说,“我不该问的,这是……”
但她打断了,“不,没关系,我不介意谈论它。去年秋天的一次钓鱼事故。在比林斯湖。他掉进湖里,撞到了头,淹死了。”
“那真是太可怕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旅行吗?”
她干笑着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在场,我本可以救他的。但是,没有,我只陪他去过一两次。钓鱼太…麻烦了。你钩住这可怜的东西,用棍子敲它的头,然后把它剖开。而且,我猜你不知道南方的规矩:妻子不钓鱼。”她抬头凝视着一些照片。他若有所思,道:“吉姆才四十七岁。我想当你和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你想到对方离世时,也会觉得他们会是自然老去。我母亲在她八十岁的时候去世了,而我父亲也是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离世,他们在一起了58年。”
“那真的很棒。”
“快乐,忠诚,奉献,”她若有所思,继续说。
洛蕾塔端来茶,像一个谨慎的仆人又端庄地走了出去。
“所以,”他说,“我很高兴,我如此温柔地搭讪的迷人女子竟然真给我打了电话。”
“你们北方小伙子都很直接,不是吗?”
“当然,”他说。
“好吧,但我希望当我告诉你我叫你来是有目的的时候,不会打击你的自尊心。”
“这取决于目的是什么。”
“生意,”桑德拉·梅说。
“生意是个好的开始,”他说着,点点头,让她继续说下去。
“吉姆去世后,我继承了公司的所有股份,当上了总裁。我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但在我看来,如果情况不能迅速改善,我们将在今年内破产。吉姆死后我得到了一些保险金,这让我不至于挨饿,但我绝不能让我丈夫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公司破产。”
“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帮你?”他的依然笑着,但是没有几分钟前那么轻浮了——比上周日好了很多。
“我妈妈曾说过‘一个南方女人必须比她的男人强壮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就是那样的女人。”
“我能看出来,”罗尔斯顿说。
“她还说,‘她也必须多一点机智’,机智的一部分就意味着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在我嫁给吉姆之前,我上了三年半的大学,但是我现在有点力不从心。我需要有人帮我,需要一个懂生意的人。听了你在周日在俱乐部告诉我的那些话后,我认为你就是那样的人。”
他们见面的时,他解释说自己是银行家兼经纪人。他收购陷入困境的小企业,扭亏为盈,然后卖掉赚钱。在亚特兰大出差时,有人建议他去看看乔治亚州东北部山区的房地产,在那里你仍然可以享受投资和度假房产的优惠价。
“跟我说说公司的情况吧,”他对她说到。
她解释说杜蒙特产品公司有16名全职员工和一群高中男生,在夏天他们从当地的林务员那里购买天然松节油,这些林业工作者通过砍伐长叶和湿地松树来获取松节油。
“我开车过来的时候闻到的就是松节油的味道。”
在几年前吉姆创办了这家公司后,桑德拉•梅躺在他的床边,就能闻着他身上油香的树脂味——即便他已经洗过澡,气味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她最终习惯了。她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不到这样刺鼻的味道的。
她继续向罗尔斯顿诉说,“然后我们将生松节油蒸馏成几种不同的产品,主要用于医疗市场。”
“医疗?”他边惊讶地问道,边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披在身旁的椅子上。喝了更多冰茶,他看起来很享受。她本以为纽约人只喝葡萄酒和瓶装水。
“人们认为它只是一种油漆稀释剂。但医生经常使用它,它是一种兴奋剂和抗痉挛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点,”他说。她注意到他开始记笔记了,调情的微笑完全消失。
“吉姆卖……”她的声音渐渐变小,“公司把精制松节油卖给几个批发商,他们负责所有的分货,我们不参与这个。我们的销售额似乎和以前一样,成本没有上升,但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了。我不知道钱去哪儿了,下个月还要支付工资税和失业保险。”
她走到书桌前,递给他几份会计报表(账本)。尽管它们对她来说是一个谜,他还是若有所思地地翻阅着,点点头,甚至有一两次惊讶地扬起眉毛。她抑制住想要询问的冲动。
桑德拉·梅发现自己正在仔细地打量他。没有了微笑,加上脸上那么一丝不苟的专注,他显得更有吸引力了。她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书柜上的结婚照,然后目光又回到了他们面前的文件上。最后他坐了下来,喝完了他的冰茶。“有件事很有趣,”他说,“我不明白。有一些现金从主账户转出了,但没有记录显示钱去了哪里。你丈夫跟你提过这事吗?”
“他没有告诉我太多关于公司的事情。吉姆不把工作和家庭生活混为一谈。”
“你们的会计怎么样?”
“大部分账本都是吉姆自己整理的……这笔钱你能追踪到吗?或者说查出发生了什么吗?不管你的标准费用如何,我都会支付。”
“我也许可以。”
她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一丝犹豫,抬起头。
他接着说到:“我先问你个问题。”
“说吧。”
“你确定要我去查明清楚吗?”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会计报表(账本),就好像它们是战场地图,“你知道的,你可以雇人来管理公司——职业商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这样对你来说会少很多麻烦,直接让他或她来扭转公司的颓势。”
她一直盯着他,“但是你并不是在问我关于麻烦的问题,对吗?”
过了一会儿,他说:“是的,我不是。我是问你是否确定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你丈夫和他公司的事情,而不是从现在起直接着手重振。”
“但现在它是我的公司了,”她坚定地说,“我想知道一切。公司现在所有的账本都在那边。”她指着一个大的胡桃木书柜。他们的结婚照就放在那件家具上面。
你是否承诺去爱、尊重、珍惜和顺从……
(译者注:美国婚礼时的誓词片段。)
当他转过身去看她所指的地方时,罗尔斯顿的膝盖擦到了她的。桑德拉·梅感到全身一阵短暂的颤抖。他似乎愣了一会儿,而后他转过身来。
“我明天就开始,”他说。
三天后,在蟋蟀和知了组成的晚间管弦乐队的演奏下,桑德拉·梅坐在他们家的门廊上……不,现在成了她的房子,这样想真是太奇怪了。不再是他们的车,他们的家具,他们的瓷器,没错,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的办公桌,她的公司……
她在秋千上来回摇晃,这是她一年前安装的,她自己把沉重的钩子拧到天花板托梁上。她眺望着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上面种着火炬花和铁杉。松溪镇有大概1600人,这里有拖车和平房,鸟笼式公寓大楼和几个中等大小的小区,但只有十几栋这样的房子——现代的、有着玻璃幕墙的、巨大的房子。如果乔治亚-太平洋铁路穿过城镇,那么吉姆和桑德拉•梅•杜蒙特定居的原始开发区就一定会决定铁路行驶的正确方向。她啜了一口冰茶,把她的牛仔套头衫弄平整,注视着六只早早到来的萤火虫发出的黄色光芒。
(译者注:玻璃幕墙,是指由支承结构体系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结构。)
我想他就是那个能帮助我们的人,妈妈,她想。
从天而降。
比尔·罗尔斯顿自从她和他见面以来,每天都来公司。他投身于拯救杜蒙特产品公司的工作。当她今晚六点离开办公室时,他还留在那里。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阅读公司的记录、吉姆的信件和日记。半小时前他打电话到她家,告诉她他发现了一些她应该知道的事情。
“过来吧,”她对他说。
“马上就到,”他回答到,她告诉了他住址。
现在,当他把车停在房子前面时,她注意到街对面房子的凸窗上出现了影子。她的邻居,贝丝和莎莉,正在查看她这边活动。所以,那寡妇有个男性朋友来拜访……
(译者注:凸窗,指凸出建筑外墙面的窗户。“凸窗”又称“飘窗”或“港湾窗”,因为这种窗户在平面形式上向室外凸出(或飘出),因此得名。)
她听到碎石上的嘎吱声,然后才在暮色中看见罗尔斯顿走近。“嘿,”她说。
“你们这里真的都这么说,”他说,“‘嘿’。”
“当然,还有是‘你们’(y’all)不是‘你们’(you all)。”
“感谢纠正,女士”
“你们北方佬啊。”
罗尔斯顿坐在秋千上,他已经南方化了。今晚他穿着牛仔裤和工作衫,还有,天啊,靴子。他看起来就像路边水龙头旁的伙计,晚上逃离妻子身边,与他的朋友们喝啤酒,和像洛蕾塔这样漂亮俏皮的女孩子们调情。
“带了些酒来,”他说。
“嗯,怎么样。”
“我喜欢你的口音,”他说。
“等等,你才是带有口音的那个。”
比尔用黑手党式的粗重而慢吞吞的语气说:“哟,别瞎扯了,我没有口音。”他们笑了,他指着地平线,“看那月亮。”
“这里没有城市,没有灯光,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星星,清晰得如同你的良心。”
他倒了些酒,还带了纸杯和开瓶器。
“哦,嘿,慢点”桑德拉·梅抬起手,“自从那次事故之后,我就没怎么喝过酒了……嗯,事故发生后,我决定还是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酒习惯比较好。”
“你想喝多少酒喝多少吧,”他向她保证,“我们会用剩下的来浇天竺葵的。”
“那是九重葛(叶子花)。”
“哦,记得吗,我是个城市男孩儿,”他拿自己的杯子碰了碰她的,喝了点酒。他轻声说,
“这一定很艰难,我是说关于吉姆。”
她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为更好的时代干杯。”
“更好的时代,”她说。他们举杯,又喝了些。
“好吧,我最好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
桑德拉·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喝了口酒,“说吧。”
“你丈夫……嗯,跟你说实话吧。他藏了钱。”
“藏?”
“嗯,这个词的确有点太过了,应该说把它们放在难以追踪的地方。看起来他在过去的几年里把公司的一部分利润用于购买一些外国公司的股票……他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是不会同意的。外国公司?我对美国股票市场都没什么信心。我认为人们应该把钱存在银行里,甚至最好是藏在床底下,这也是我妈妈的哲学。她称之为国家第一床行。”
他笑了。桑德拉·梅喝完了她的酒,罗尔斯顿又给她倒了一些。
“总共有多少?”她问他。
“20万多一点。”
她眨了眨眼睛,“天哪,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它,越快越好。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是有的,但你丈夫真的很谨慎。”
“谨慎?”她强调这个词。
“他非常想隐藏这些资产。如果我能知道他为什么想这么做,就容易多了。”
“我毫无头绪,”她抬起手,而后落在她结实的大腿上,“也许是退休金。”
但是罗尔斯顿笑了。
“我说了什么傻话?”
“401K才是你存退休金的地方,开曼群岛可不是。”
(译者注:1、401k,指401k退休计划,是美国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2、开曼群岛是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开曼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亦是世界著名的潜水胜地、旅游度假圣地。金融和旅游业是其主要经济来源。)
“吉姆做的事违法吗?”
“不一定,但也有可能,”他喝光了杯子里的酒,“你想让我继续吗?”
“是的,”桑德拉·梅坚定地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你找到什么。我必须得到那笔钱。”
“那我就照做。但这会很复杂,真的很复杂。我们得在特拉华州,纽约和开曼群岛提出诉讼。你能一次离开这里几个月吗?”
停顿了一会儿,“可以,但是我不想,这是我的家。”
“好吧,你可以授权我来处理这件事,但是你并不了解我。”
“让我想想,”桑德拉·梅把发夹从头上取下来,让金色的发丝自由散落。她仰着头,望着天空,看着星星,看着那迷人的月亮,月快满了。她意识到她并没有靠在门廊秋千后休息,而是靠在罗尔斯顿的肩膀上,她没有移开。
接着,星星和月亮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黑暗的轮廓,他吻了她,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脑勺,然后是她的脖子,接着滑到她的针织套衫前,解开系着肩带的纽扣。她用力回吻了他,他把手伸到她的喉咙上,解开了她上衣最上面一颗扣子,那是她系紧的——她母亲告诉她,淑女总是应该这样做。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比尔·罗尔斯顿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她抬头看着天花板。焦虑又回来了,她害怕失去一切。
哦,吉姆,会发生什么?她想起了她那躺在松溪纪念花园的红土里的丈夫。
她回想起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没有按照她的计划发展——想着她是如何在毕业前六个月从乔治亚州立大学退学去选择和他在一起的;想着她是如何放弃了自己从事销售工作的希望的;想着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趋于一种常规:吉姆管理公司,而她招待客户,在医院和妇女俱乐部做志愿者,管理家务。这本该是一个满是孩子的家庭——这正是她所希望的,但这从未实现。
现在桑德拉•梅•杜蒙特只是个没有孩子的寡妇……
松溪镇的人就是这么看她的,镇上的寡妇。他们知道公司会倒闭,她会搬进沙利文街上那些糟糕的公寓里,然后消失,成为南方小镇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她的未来没有更好的看法,但这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
不会的,女士……她还是可以找到另一半,重组家庭。她很年轻,她可以去别的地方,大城市,也许——亚特兰大、查尔斯顿……见鬼,为什么不去纽约呢?
一个南方女人要比她的男人强壮点,也更加机智。她会摆脱这个烂摊子。
罗尔斯顿可以帮她摆脱困境。她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选择了他。第二天早上,当她醒来时,桑德拉·梅发现她的手腕抽筋了:她睡着时,双手紧握成拳头。
两个小时后,当她到达办公室,洛蕾塔把她拉到一旁,用涂着黑色睫毛膏的眼睛直盯着她的老板,低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杜蒙特夫人,但我觉得他想要卷走你的钱。我是说,罗尔斯顿先生。”
“说说看。”
桑德拉·梅皱着眉头,慢慢地坐在高靠背皮椅上,又看了看窗外。
“好吧,你看,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冷静下来,洛蕾塔。告诉我。”
“你看,昨晚你走后,我把一些文件带到你的办公室,我听到他在打电话。”
“他在和谁说话?”
“我不知道。但我朝里面看看了看,他用的是手机,而不是他通常使用的办公室电话。我觉得他用了那部手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他打给谁的记录了。”
“先别急着下结论,他说了什么?”桑德拉·梅问道。
“他说他很快就能找到所有东西了,但要想逍遥法外(get away with it)会是个问题。”
“‘逍遥法外(Get away with it)’,他是这么说的?”
“是的,女士。对,对,没错。然后他说一些股票什么的都是公司持有的,不是‘她个人持有的’,这可能是个问题。这是他的原话。”
“然后呢?”
“哦,然后我撞到了门上,他听到了,很快就挂了电话。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卷走钱,”桑德拉·梅说。“逃脱惩罚(Get away with it),也许这仅仅针对的是从外国公司那里拿到资金,或者他说的是别的什么。”
“当然,杜蒙特夫人,也许是这样。但当我走进房间时,他就像一只受惊的松鼠,”洛蕾塔用她长长的紫色指甲拂过她的下巴,“你有多了解他?”
“不太了解……但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吗?”桑德拉·梅摇了摇头,“不可能,我打电话是想叫他来帮助我们。”
“但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桑德拉·梅沉默了,而后她说,“他遇到了我……好吧,他来接我,算是吧,在松溪镇俱乐部。”
“然后他告诉你他是做生意的。”
她点点头。
“所以,”洛蕾塔指出,“他有可能听说你继承了公司,故意去那里见你。或许他就是和杜蒙特先生有生意往来的那些外国公司的人之一,并且做了一些不太对劲的事。你刚才是怎么跟我说的?”
“我不相信,”桑德拉·梅抗议道,“不,我不相信。”
她看着助理的脸,她的脸很漂亮,很端庄,是的,但也很精明。
洛蕾塔说,“也许他在寻找那些经营企业困难的人,然后搬进来,砰的一声,把它们一扫而光。”
桑德拉·梅摇了摇头。
“我也不能肯定,杜蒙特夫人。我只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你。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根本不能失去我们的工作。”
“我可不想做一个胆小怕黑的寡妇。”
“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阴影,”洛蕾塔说。
“亲爱的,我和他谈过了,看着他的眼睛,”桑德拉·梅说,“我想我和我妈妈一样善于看人。”
“我希望你是对的,女士,为了我们所有人,我希望你是。”
桑德拉·梅的眼睛又扫视了一遍办公室,她看到了丈夫带着他打包的鱼和猎物的照片,看到了早期公司的照片,看到了新工厂的奠基仪式,看到了在扶轮社的吉姆,看到了吉姆和桑德拉·梅自己坐着公司的花车,当时是在镇集市。她还看到了他们的结婚照……
(译者注: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亲爱的,你那漂亮的小脑袋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一切都会没事的。别担心,别担心,别担心……
她丈夫对她说过一千遍的话在她脑海里反复回响。桑德拉·梅再次坐在办公椅上。
第二天,桑德拉·梅发现比尔·罗尔斯顿在办公室里,弓着身子看着一本会计账簿。她把一张纸放在他面前。
他抬起头,皱着眉。
“这是什么?”
“说的那份委托书。它给了你权力去找到我们的钱,提出诉讼,给了你公司股份的投票表决权,还有所有的一切……”她笑了,“我得说我对你有些怀疑。”
“因为我来自纽约?”他微笑着。
“北方侵略战争,为什么,它有时会露出丑陋的头……但是,不,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给你。因为一个寡妇不能害怕自己的影子。人们能看到且能感觉到水中的鲜血,接下来你知道的,就是再见了。不,不,我看着你的眼睛对自己说,我相信他。所以现在我要说到做到,或者,我应该说用的是我丈夫的钱。隐藏的资产,”她看了看文件,“在吉姆出事之前,我会带着问题去找他。在吉姆之前,我会去找我妈妈。我不会做任何决定,但我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必须自己做决定。其中一个选择就是雇佣你,信任你,这是我为自己做的事。现在,用这个把钱找回来。”
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委托书,注意到上面的签名,“这份委托书是不可撤销的,你不能收回它。”
“律师说,如果你需要追踪资金和提出诉讼,可撤销的证书是没有用的。”
“很好,”他又给了她一个微笑。但是和之前不一样了,他的表情有一种冷漠,甚至还有一丝胜利的迹象——就像你在松溪镇高中的红脖子((对美国受教育不多且政治观点保守的乡下人的贬称))的脸上能看到的那样。
“啊,桑迪,桑迪,桑迪——我告诉你,我原以为还要花几个月呢。”
她皱起了眉头,“几个月?”
“是的,女士,我是说控制公司。”
“控制?”她盯着他,呼吸变得急促。
“你在……你在说什么?”
“这可能是一场噩梦——最糟糕的是,我不得不在这个鬼地方呆上不知多久——松溪镇……”他用乡下人的口音,讽刺地说,“上帝啊,你们这儿的人怎么会不发疯呢?”
“你在说什么,”她低声道。
“桑迪,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的公司,”他轻拍着委托书,“我会投票选举自己当上总裁,给自己发一份丰厚的薪水和奖金,然后卖掉这个地方。你会赚到钱的——别担心。你仍然是股票的持有者。别担心那些隐藏的钱,它们根本就没有被藏起来。就像过去其他大多数商人一样,你丈夫把公司的一些钱投资到海外。市场下跌时他受了点损失,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它会回来的,你甚至从未濒临破产。”
“为什么……”她倒吸一口凉气,“你这该死的混蛋!这是诈骗!”她伸手去拿委托书,但他把她的手推开了。
罗尔斯顿伤心地摇了摇头,然后停了下来,皱着眉头。他注意到桑德拉·梅脸上的愤怒变成了笑容,接着笑出了声。
“什么?”他不确定地问。
她向他走去,罗尔斯顿抓起委托书,小心翼翼地向后退去。
“哦,放放松,我是不会打你的头的——尽管我应该这么做。”桑德拉·梅俯身越过他,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
“什么事?”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
“洛蕾塔,你能过来一下吗?”
“当然,杜蒙特夫人”
洛蕾塔出现在门口。桑德拉·梅的眼睛还盯着罗尔斯顿。她说,那份委托书给了你对我所有的股份投票表决权,对吧?”
他瞥了一眼夹克的口袋,文件现在就放在那里,他点点头。桑德拉·梅继续对洛蕾塔说道,“我持有公司多少股份?”
“没有,杜蒙特夫人。”
“什么?!”
桑德拉·梅说,“我们猜到你会想耍什么花招,所以我们必须测试下你。我跟我的律师谈过了,他说我可以把股份转让给我信任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持有任何股份了。然后我会签署委托书,交给你,看看你会做什么。我很快就明白了你打算把我洗劫一空,这是一次考验,而你失败了,先生。”
“该死的,你转让了股份?”
她笑着向洛蕾塔点点头,“是的,给了我可以信任的人,我一点也没有。那份委托书毫无用处。她才拥有杜蒙特产品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但是罗尔斯顿的震惊消失了,他开始微笑。
他心情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而是由于洛蕾塔。她说:“你现在听着。你绝对猜不到,是比尔和我拥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抱歉,亲爱的。”她走上前去,搂着罗尔斯顿,“我想我没有没提到过,但比尔是我弟弟。”
“你们是一伙的!”桑德拉·梅低声说,“你们两个。”
“吉姆死了,一分钱也没留给我!”洛蕾塔厉声道,“那笔钱是你欠我的。”
“吉姆为什么要给你留东西?”桑德拉·梅不确定地问,“为什么……”但是当她看着瘦削女人脸上会意的笑容时,她的声音变弱了。
“你和我丈夫?”桑德拉·梅喘着粗气,“你们在交往?”
“过去三年一直如此,亲爱的。你没注意到是我们同时出城吗?没注意到我们会在同一个晚上工作到很晚吗?吉姆是在为我存钱!”洛蕾塔全说了出来,“他只是在死前没有机会给我。”
桑德拉·梅跌跌撞撞地倒在沙发上。“股票……为什么,我那么信任你,”她喃喃地说,“律师问我能相信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就像我信任吉姆一样,”洛丽塔厉声回答,“他一直说他会给我,他会为我开个账户,我能去旅行,他会给我买一栋漂亮的房子……但后来他死了,没给我留下一分钱。我等了几个月,然后给在纽约的比尔打了电话。我把你和公司的事都告诉他了。我知道你周日要去松溪镇俱乐部。我们觉得他应该过来向那个可怜的寡妇做个自我介绍。”
“但你的姓氏不一样,”她对罗尔斯顿说,拿起他的一张名片,瞥了一眼洛蕾塔。
“嘿,这没那么难懂,”他说着,抬起了手,“这是假的。”他笑了,就好像这些都太明显了,连提都不值得提一样。
“当我们卖掉公司的时候,亲爱的,你会得到一些东西的,”洛蕾塔说,“不要为此烦恼,感谢你你担任总裁的最后六个月。现在,你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呢?你不介意我不再叫你杜蒙特夫人了吧,桑迪?我真的讨厌——”
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
“桑德拉·梅,你没事吧?”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门口,是博·奥格登,镇警长。他把手放在手枪上。
“我很好,”她告诉他。
他看了看罗尔斯顿和洛蕾塔,后者不安地盯着他。
“就是他们?”
“没错。”
“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赶来了。”
罗尔斯顿皱着眉头,“什么电话?”
奥格登警告说:“把你的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该死的,你到底在说什么?”罗尔斯顿问。
“请保持礼节。放尊重,先生,你不想让自己的问题变得更糟。”
“警官,”洛蕾塔说,声音听起来非常平静,“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些生意,仅此而已。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有合同,文件等等。杜蒙特夫人以10美元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我,因为公司负债累累,她认为我和我弟弟可以扭转局面。自从我为她丈夫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不亚于我对她的了解。是她自己的律师做的交易,作为她的前雇员,我们会支付她一笔赔偿和解金。”
“是啊,这些都无所谓,”奥格登心不在焉地回应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走进办公室的一个年轻的、留着平头的副手身上。“吻合,”他告诉警长。
奥格登朝洛蕾塔和罗尔斯顿点点头,“把他们两个都铐起来。”
“没问题,博。”
“把我们铐起来!可我们什么都没做!”
奥格登坐在桑德拉·梅旁边的椅子上。他严肃地说:“我们找到了。不过不是在树林里,是在洛蕾塔家的后门廊下面。”
桑德拉·梅伤心地摇摇头,拿起纸巾擦了擦眼睛。
“找到什么?”罗尔斯顿厉声问道。
“你们两个还是坦白吧,我们知道所有事。”
“什么事?!”洛蕾塔朝桑德拉·梅吼道。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后挣扎着回答,“我就知道有些事不对劲,我发现你们两个想骗我——”
“她只是个可怜的寡妇,”奥格登喃喃地说,“真可耻。”
“所以我今早上班前给博打了电话,告诉了他我的怀疑。”
“警长,”洛蕾塔继续耐心地说,“你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她自愿把股票转给了我。没有欺诈,没有……”
警长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洛蕾塔,你被捕是因为你对吉姆的做的事,而不是什么欺诈之类的。”
“你对吉姆做了什么?”罗尔斯顿看着妹妹,妹妹摇了摇头,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因涉嫌谋杀吉姆·杜蒙特被捕。”
“我没有谋杀任何人!”罗尔斯顿脱口而出。
“你的确没有,但她确实这么做了,”奥格登对洛蕾塔点点头,“这样一来,你就成了共犯,而且很可能还犯了同谋罪。”
“不!”洛蕾塔尖叫道,“我没有。”
“几周前,一个在比林斯湖边拥有一间小木屋的人自告奋勇说,他在万圣节前后看到一个女人和杜蒙特先生一起去钓鱼。他看不太清楚,但他说看起来她似乎拿着一根棍棒还是树枝。这家伙没想太多,离开了小镇一段时间。他很快就回来了——上个月——听说吉姆去世了,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过验尸官,他说 杜蒙特先生摔倒的时候很可能没有撞到头。也许是他被人打了,然后被推进了水里。所以我重新立案,将这起案子作为谋杀案调查。过去一个月我们一直在调查目击者和法医结论,认为这绝对是谋杀,不过我们找不到凶器。然后杜蒙特夫人今早打电话给我说了你们俩的事还有这个骗局之类的,这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杀人动机。我让地方法官签发了搜查令。这是我们在你门廊下找到的,洛蕾塔:杜蒙先生用来杀鱼的警棍,上面有他的血迹和头发。我还找到了你打他时戴的手套。女士手套,还挺时髦。”
“不,不是我干的,我发誓。”
“宣读他们的权利,迈克。这也得做好,不要留任何漏洞。另外,把他们赶出这里。”
罗尔斯顿喊道:“不是我干的!”
副警长按照指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领了出去,奥格登警长对桑德拉·梅说,
“真有意思,他们都这么说。打破纪录。‘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我真的很抱歉,桑德拉·梅。刚失去吉姆就已经够艰难的了,还陷入这些蠢事。”
“没关系,博,”桑德拉·梅说着,一边故作端庄地用纸巾擦眼睛。
“我们想录一份口供,但不必着急。”
“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警长,”她坚定地说,“我想让这些人离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会确保这一点的,祝你好运。”
警长离开后,桑德拉·梅独自站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她丈夫几年前拍的照片。他手里拿着一条钓到的大鲈鱼——可能是在比林斯湖钓到的。然后她走到外面的办公室,打开迷你冰箱,给自己倒了一杯甜茶。
回到吉姆的办公室,不,是她的办公室,她在皮椅上坐下来,慢慢地转着圈,听着现在已熟悉的机械装置发出的吱吱声。
心想:好吧,警长,你几乎全对了。
只是这个故事需要小小改变一下。
那就是桑德拉·梅一直都知道吉姆和洛蕾塔的事。她已经习惯了丈夫皮肤上松节油的味道,但是从来没有习惯过那女人的垃圾香水味,当他爬上床的时候,那味道就像一团臭气般弥漫在他周围,他累得连吻她的力气都没有。(“如果一个男人一周不会要你三次时,桑德拉,你最好开始想想为什么。”谢谢你,妈妈。)
(译者注:松节油,是精油的一种,它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通过蒸馏或其他方法从松柏科植物的树脂所提取的液体。)
所以当吉姆·杜蒙特去年10月开车去比林斯湖的时候,桑德拉·梅跟着他,质问他关于洛蕾塔的事。当他承认的时候,她说,“谢谢你没有撒谎,”接着拿起警棍,一棍子打碎了他的头骨,然后把他踢进了冰冷的水里。她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吉姆的死被判定为意外死亡,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个案子——直到比林斯湖的那个男人站出来,宣称在吉姆死前看到一个女人和他在一起。桑德拉·梅知道他们迟早会查出她是凶手。
无期徒刑的威胁——不是公司的状况——才是她发现自己陷入的可怕麻烦,也是她祈求“从天而降”的帮助所需应对面临的困境(至于公司?谁在乎呢?所谓吉姆留的“一些保险金”总计近一百万美元。为了逃脱惩罚,她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杜蒙产品公司破产,放弃吉姆为他那瘦猴荡妇攒下的钱。)她怎样才能免于牢狱之灾呢?当罗尔斯顿来接她的时候,她有了答案。他太狡猾了,她察觉到了这一个骗局,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他和洛蕾塔的联系。她觉得他们打算把公司从她身边夺走。”
所以她自己想出了一个计划。
桑德拉·梅打开桌子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小瓶肯塔基波旁威士忌(波本威士忌),往冰茶里倒了三指的量。她坐在丈夫以前的椅子上,现在这把椅子只属于她了,她凝视着窗外,一片高大的黑松林,在春天的暴风雨中弯曲着。
罗尔斯顿和洛蕾塔啊,我从未告诉过你们妈妈那句话接下来是什么,对吗?
“亲爱的,”老妇人对她的女儿说,“一个南方女人必须比她的男人强壮点。她也必须多一点机智。而且,私下告诉你,还要更加阴险一点。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桑德拉·梅·杜蒙特喝了一大口冰茶,给旅行社打了个电话。 |